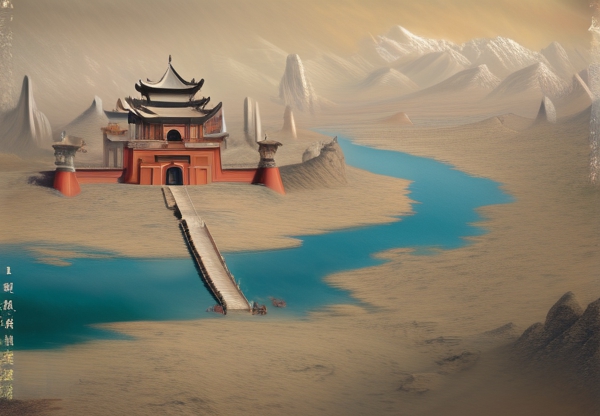
今天是23日,一则关于中亚地区"中文社区"的争议性报道在网络上持续发酵。在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塔拉斯州、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州等地,存在着一个现象级的族群:他们能流利使用汉语方言进行日常交流,部分长者仍能哼唱《孟姜女》《白蛇传》等中国民间小调,却在百余年前完全停止了汉字书写。这一"有声无字"的文化断层,与清朝在西域的统治历史存在何种关联?
要解开这个谜题,必须回溯到19世纪中后期。随着清朝对新疆的治理加强,部分满汉官员、回部工匠、商贩等群体迁入中亚贸易要道。据清廷《同治新疆识略》记载,1870年代有超3万名汉语使用者在今塔吉克斯坦瓦罕走廊等地留下定居点。他们随后与当地塔吉克、哈萨克族通婚,形成了特殊的双语社群。但19世纪末沙俄与清朝在边境划定的博弈,成为这些人文化转向的关键转折点。
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库尔干州一座帕米尔高原村庄,我们采访到78岁的伊利亚斯·阿塔耶夫。他指着世代传承的"神秘符号册"说:"我们祖辈用毛笔记录的\'汉字\',当地人都叫它\'tushu\',实际早已变异为仅存78个记音符号。"这种独特文字系统印证了语言学家的发现——社群在189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放弃汉字,转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。这恰与沙俄推行"语言审查政策"同步发生。
如今这个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发新思考。彭博社23日发布的跨境人口报告显示,中亚西突厥斯坦地区仍有约14万代际相传的汉语使用者,但他们中仅有0.7%能书写汉字。当笔者询问正在中国留学的第三代后裔艾莎·梅利舍娃时,她坦言:"我们从小在家说\'卷舌tongue\',在学校学俄语,看汉语电视剧会切换越南字幕——就像活在语言的夹缝里。"这种文化割裂感,恰恰折射出族群认同困境的现代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,部分学者将此现象与近日火热的"多语种数字身份"概念相联系。正如《纽约时报》新近披露的元宇宙语言保护试验,中亚华人使用的"拼音化汉语"可能成为传统汉字之外的"平行文化载体"。这种文化折衷主义在地区冲突频发的当下,反而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——他们用手机输入法创作的汉维双语诗歌,在TikTok上获得超200万次播放。或许正如人类学家王 Chips 所言:"语言不是静止的化石,而是流动的活水。"
当我们将视角拉回历史现场,会发现清朝的政治决策如何悄然改变文化命运。1881年《中俄伊犁条约》签订后,清朝撤军导致中亚汉语社群失去母国支援。沙俄随后实施"去汉字化运动",1903年法令明文禁止使用汉字文书,使原来能写两句毛笔字的商人都变成了"文字盲"。这种文化的"格式化",恰与当代塔利班禁止女性读书的悲剧形成跨时空对照,警示着政治强权对文化的破坏力。
在跨境婚姻成为新趋势的今天,这个族群的汉语正在经历奇特变异。学者比对发现,其语言保留了18世纪河南、陕西方言特征,如"moshi"(母亲)、"tersi"(葡萄),却混入大量突厥语构词法。这种"混血语言"的活力,使得美国国家地理"濒危语言保护项目"将其列为优先对象。3月刚发布的修订版濒危语言地图上,这种中亚汉语标注为"严重濒危",其生态堪比北极格陵兰鲸。
站在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角度审视,这个群体的选择既是历史暴力的遗产,也是能动性的创造成果。正如民族志电影导演吴清遥在纪录片《喀喇昆仑的舌头》中展现的:老人们坚持用汉语给新婚夫妇唱祝福歌,年轻人用阿拉伯字母标注方言俗语词典,孩童在麦当劳广告里捕捉"发券"(free coupon)的语音残片——每个瞬间都在重构着没有文字伴随的语言身份。
这或许正是文明传承最本质的模样。当我们讨论"文化记忆"时,不应执念于文字书写形式,而应关注语言背后的情感纽带和生存智慧。正如那些在丝绸之路故道上,用汉语唱着"月儿明, C?ng (工作),人平安"民谣的牧民,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诉说着:文化的生命力,在于主动选择成为过去与现时的中间态,而非僵化的标本。这种充满张力的生存策略,或许比任何文物档案都更能诠释"何以为我"的终极命题。
P>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新疆与中亚文化交响的历史脉络,可浏览中亚的特殊“华人”:万人为什么说着中文,却弃用汉字清朝西域专题数据库,这里保存着200余卷社区口述史档案和语言样本录音。在地区局势变幻的今天,这个群体更像是文化融合的活体实验室:他们证明语言可以摆脱文字而独立存活,族群认同能超越书写的束缚,多文化元素在撕扯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性。或许这正是文明长河给予当代人最温柔的启示——只要还能哼唱祖辈的歌谣,文化就不会真正消亡。